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只要一天它們還在,那世界還是很美好。
 蘇格蘭有一個愛觀星的男人,為了要跟星空親近,到一個孤島當上燈塔管理員,每隔半年,才放假回家跟妻子相聚;平日陪伴他的,就只有幾隻羊,以及數不清的海島。
蘇格蘭有一個愛觀星的男人,為了要跟星空親近,到一個孤島當上燈塔管理員,每隔半年,才放假回家跟妻子相聚;平日陪伴他的,就只有幾隻羊,以及數不清的海島。 《武陵春》
《武陵春》 Nothing has changed.
Nothing has changed. It could have happened.
It could have happened.
You survived because you were the last.
Because you were alone. Because of people.
Because you turned left. Because you turned right.
Because rain fell. Because a shadow fell.
Because sunny weather prevailed.
You were in luck - there were no trees.
You were in luck - a rake, a hook, a beam, a brake,
a jamb, a turn, a quarter inch, an instant.
You were in luck - just then a straw went floating by.
As a result, because, although, despite.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a hand, a foot,
within an inch, a hairsbreadth from
an unfortunate coincidence.
So you're here? Still dizzy from another dodge,
close shave, reprieve?
One hole in the net and you slipped through?
I couldn't be more shocked or speechless.
Listen,
how your heart pounds inside me.
威廉斯這本"懺悔錄"從他少年落拓江湖,壯年叱吒風雲,一直寫到他晚年鬱鬱寡歡,眾叛親離。這本自傳的形式相當特別,完全是意識流式的自由聯想,時間跳前跳後,很像一出新潮電影。人名地名,五色繽紛,令人目不暇接,但史實並非這本書的重點,事實上威廉斯常常記錯日期事實。這本自傳感人的地方在於威廉斯對他的戲劇創作鍥而不捨,鞠躬盡瘁的精神,以及他在愛與欲之間的彷徨、沉淪、追悔、煎熬。戲劇創作與愛欲的追逐佔有了他整個的人生,而前者又遠重於後者,後者只是前者的燃料。他的好友伊曆卡山評論威廉斯:"他的生命都在他的作品裏。"這是知言。只有瞭解了威廉斯對他的創作是如何的執著嚴肅,我們對他放浪形骸的生涯才會寬容諒解。威廉斯一生中寫下了數量驚人的作品:二十五出長戲、四十個短劇、兩本長篇小說、六十個短篇小說,還有一百多首詩。他在酗酒服藥的時候,不停的寫作,滿街追逐男孩子的時候也沒有忘記寫作,他明知自己的創作力逐漸衰退,但他仍然鼓起勇氣,奮筆直書。他的每一天,似乎都是為寫作而活的。威廉斯的健康一直不好,一身的病,但居然活到七十二歲,是創作支撐了他的生命。


「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家具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摘自《親愛的安德烈 藏在心中的小鎮》,蘋果日報,17-7-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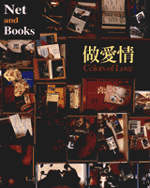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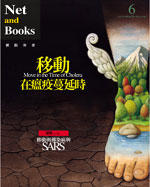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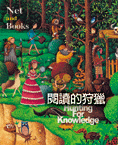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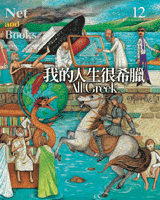





《從大英圖書館的下午談起》 郝明義
2001年 3月底,我參加倫敦書展。書展之後,有一個下午在大英圖書館讀書。
倫敦固然以陰冷聞名,今年又特別。
書展會場,一位莫斯科來的出版同業就說真不知道倫敦的三月可以冷到這種地步。那天下午,卻是陽光明媚。所以到了大英圖書館外,沒有進去,先在廣場上曬著太陽小睡了片刻。我去圖書館,一方面是慕名,一方面是想找一些書。當時《網路與書》的試刊號已經出版,聽過各方意見後,想整理一下思緒,也想為自己要寫的一篇文章找一些資料,因此到大英圖書館去一趟,就成了心底很大的期待。
要進大英圖書館的研究室,需要申請。他們問我有什麼要研究的主題,我說讀了些西方印刷術與西方文明關係的書之後,想來找一些中國印刷術和東方文明相關的閱讀。圖書館新擴建過,透著天光的大廳,泛著光亮的大理石地板,十分怡然。到樓上,進了研究室,卻又是另一種氣氛。滅音的地毯,一排排卡片櫃,一些電腦檢索的螢幕,是最先映進眼廉的。再進去,就是一排排開架式的書架,和一排排閱讀檯。有一位中文室主任,和一位日文室主任出來見我。他們又再問一遍我來的目的。聽過之後,日文室主任走過書架,找了兩本書給我。中文室主任找了三本書給我,然後告訴我如果還要找相關的書,可以去書架的哪個區域尋找。
那天下午,我就在那裡翻閱了他們推薦的五本書(時間來不及細讀)。我有兩個深刻的感觸。其一,是佩服那兩位主任分別推薦給我的三本書,兩本書。大英圖書館藏書之豐,不必多言。他們如果很輕快地指出幾萬幾千,或幾百種可能是我需要的書目,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或者,如果他們端出幾十種書給我,也屬正常。我佩服他們只推薦三本、兩本書。那不是草率,也不是武斷,而是一種對自己館藏圖書了然於胸的信心之中,還帶著對讀者的體貼。體貼讀者從最方便的入口進去摸索一條閱讀的途徑。英文所謂的Librarian,中文實在不該譯為「圖書館員」。其二,是對參考書目有了新的想法。除了那五本書之外,那天下午我也忙於從書後所列的參考書目,以及他們所告訴我的那塊書架區域之間尋找驚喜。
雖然以前也使用參考書目來當作閱讀的參考,但沒有像那天下午那麼深刻的感受。不是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大英圖書館,也不是每個圖書館裡都有那麼專業又體貼的Librarian,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彌補這些不足?每一本書的作者,其實都可以扮演一個Librarian的角色。書後所列的參考書目,很像作者這個Librarian所指出另一塊無形的書架區域。我們從閱讀一本書的本文到徜徉於書後的參考書目,以及從參考書目中的某一本書再由本文而搜尋列於其後的參考書目,這種延伸,就是網路。對作者來說,為了寫作的嚴謹,參考書目固然需要列得鉅細靡遺,但是為了方便讀者進入他思想的領域,顯然應該在參考書目中另闢一個特別推薦的角落。
在《網路與書》試刊號〈密林裡尋找一片樹葉的探險〉文章裡,我說過「網路,是一種新型態的書。書,是一種傳統型態的網路。」那天下午,特別清楚地看出「書,是一種傳統型態的網路。」大英圖書館的經驗,對我接下來思考《網路與書》的編輯方向時,助益匪淺。我一直提醒自己,如何進行歸納與延伸──不論就整本刊物,還是就單篇文章。換句話說,如何提供那兩本、三本的門戶,以及其後的聯結。方向有了,但方法還是相當混沌,怎樣把這樣一個方向轉化到雜誌的表現型態,固然有趣,但也有些扞格之處。這些想法,等到我們實際做完台灣都會區閱讀習慣調查之後,有了進一步的釐清。這次調查的結論,都在本書第56到69頁,這裡就不再重複。
從大英圖書館的那個經驗,加上這次調查報告的結論,我發現就閱讀是「密林裡尋找一片樹葉的探險」而言,與其以話題導向的月刊型態來出版《網路與書》,不如以主題導向的書的型態來出版《網路與書》。只是這樣的書,在編輯與設計上,可以加入許多雜誌的概念與光影。這就是各位看到新的內容與形式的《網路與書》,以及這個系列裡的第一本書《閱讀的風貌》。非常感謝所有讀者從《網路與書》試刊以來的支持與容忍,使得我們在思考未來的方向時,一直有著最大的空間。